美国是一个移民之邦, 从1607年始至今已融合了100多个民族成分, 种族之杂糅位世界之最。进入20世纪80年代, 百万计的东南亚及拉美国家的移民涌进美国。他们的到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新的移民浪潮使美国国内已沉寂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移民问题辩论再度在全美国范围内爆发。本文拟从美国移民辩论问题入手, 考察移民辩论的历史轨迹, 透视美国各阶段移民辩论的主题、论点及特征, 解析美国移民辩论的思想体系。
一
美国学者马克辛·塞勒在其《美国移民政策的历史透视》一文中将美国历史上对移民辩论
分为四个时期: 殖民地时期(1720- 1776年); 南北战争以前(1830- 1860年); 新移民时期
(1882- 1924年); 东南亚及拉美移民时期(1980年)。塞勒认为, 每一次辩论必定会导致美国
移民政策的变化, 因此他对移民大辩论时期的划分主要依据移民政策的变化, 并将这四次辩论称作美国移民政策大辩论。另一位美国学者威廉·伯纳德在其为《哈佛美国种裔集团百科全书》撰写的论文中, 将美国移民政策辩论划分为五个时期: 殖民时期(1609- 1775年); 门户开放时期(1776- 1881年); 控制时期(1882- 1916年); 限制时期(1917- 1964年); 自由化时期
(1965年—)。塞勒和伯纳德的时期划分有一个共性, 即把移民大辩论置入移民政策制定的大
框架里。但美国历史上关于移民的辩论不仅仅局限于对移民政策的辩论, 还包括对经济、文化、种族和宗教等诸多方面的辩论。这些非政策性的主题辩论最终导致移民政策的制定、修改。然而, 一项移民政策的出台并不表示移民问题辩论的终结, 相反却引发一场更大的移民辩论。因此, 按照移民政策的出台来划分移民辩论的时期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移民大辩论的历史轨迹。依据对美国移民辩论的历史考察, 参照塞勒和伯纳德的时期划分, 笔者认为美国移民大辩论共有四个阶段: 独立战争前后(1720—1812年); 南北战争以前(1820—1860年); 新移民时期(1880—1924年); 东南亚及拉美国家移民时期(1980年—)。四个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一)18世纪至19世纪初德国人和苏爱人的大量涌入美国, 其数目之大引起美国人的恐慌, 特别是德国人对德语的强烈情结是第一次大辩论的导火线。1720年以前, 德国移民在形式上是以个人身份掺杂在荷兰人的移民队伍中的。来美后, 由于人数极少, 加之融入其他民族之中, 因而他们对母国的情结及认同因受新环境的制约而未能形成一种族裔性。但在1720年以后, 特别是在1740—1760年间, 仅在费城码头上岸的德国移民就达6万人。1745年, 宾夕法尼亚集聚了约45, 000德国人。德国移民人数之大, 人口之集中曾一度引起该州粮价上涨, 因而导致早期定居者对德国人的不满和排斥。此间, 大量苏爱人也聚居在宾夕法尼亚中部, 该民族因爱打斗、酗酒而恶名远扬。虽然, 德国人在气质和举止方面与苏爱人迥然不同, 但由于德国人对德语的情结之深, 他们坚持讲德语的习惯令操英语的殖民地居民不安。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宾夕法尼亚将在几年时间内成为德国殖民地。他们不学习我们的语言, 相反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 否则我们就像生活在异国里。”同年, 他又警告道: “我想用不了几年的功夫, 在议会中就需要有译员来把这一半议员的发言翻译给另一半议员听。”德国人的德语情结、苏爱人的恶习, 是引起第一次移民大辩论的主要原因。但随着独立战争的爆发, 德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英勇作战使美国人对德国人的心理恐惧减弱。加之苏爱人、德国人与美国早期定居者在人种上相承, 他们对美国的认同和融入主流社会的速率较快, 因而第一次移民大辩论持续较短,范围较小。尽管如此, 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的1798年, 国会仍通过了《外侨叛乱惩治法》, 以防止“国中之国”和惩罚任何对共和国的背叛行为。此后, 1793年至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和1812至1814年的英美战争几乎完全中断了欧洲移民潮, 美国移民问题不再明显。
(二)1820年至1880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大潮。在这场移民潮中, 共有1000万移
民来自北欧和西欧, 其中大部分为英格兰人, 其次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 兼之少量亚裔移民。依据美国移民归化局统计数字, 1820至1840年间移入美国的爱尔兰人达2612万人, 德国人为16万人。1841—1880年爱尔兰人数猛增到25617万人, 德国人为28912万人。美国天主教教徒也因德国教徒和爱尔兰教徒的加入, 从1810年的715万猛增至1860年的300多万, 占当年美国总人口的10%左右。由于英格兰移民属盎格鲁2撒克逊脉系, 引起这期间移民大辩论主要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强烈的天主教宗教观。为维护“新教”的地位, 反对“异教”的侵蚀, 一种“本土主义”意识在美国人中滋生。本土主义者高举“美国是美国人的”大旗, 烧毁修道院, 将牧师从布道台上赶走。他们对异邦人持怀疑态度, 认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对“天主教”的忠诚将削弱其对美国的忠诚。他们甚至预见到天主教信徒人数的增长最终将以教皇代替美国总统。在这种极端恐外思想支配下, 他们把“异教”和“异国文化”视作美国同质文化的潜在威胁。1836年, 电报发明人塞缪尔·F. B. 莫尔斯建立了第一个本土政治组织——“纽约本土美国人民主协会”。该组织的“反移民”立场, 特别是反天主教的情绪把第二次移民大辩论推向高潮。1844年, 一个新的本土主义组织——“美国共和党”成功地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麻省选出了为数可观的州级官员。这些官员及其追随者致力于“排斥移民”活动。1845年7月4日, 他们在费城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将“美国共和党”正式改名为“美国党”并通过了“反移民纲领”。这个反移民纲领的核心就是主张“美国是美国人的”。从1845至1855年10年间, 美国党已吸收了100万名成员, 其倡导的“无所知运动”将反移民情绪推向全国。1855年美国党推出本党总统候选人, 但未获成功。内战爆发后, 美国公众的注意力转向奴隶制问题, 美国党失去舆论支持, 随之夭折, 移民辩论浪潮也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和反移民势力的减弱暂告一段落。但美国党的反移民纲领构建了美国排外主义的思想基础。
(三)1860年之前, 移民主要来自德国、爱尔兰和英国, 而1860年后, 移民大多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国及南美, 主要参加美国西部开发和铁路建设。据美国政府统计, 截至1870年,在美国淘金的华人有117万, 占淘金总人数的11%。在俄勒冈, 华人矿工占当地矿工的61%;
在蒙大拿, 华人占21%; 在爱达华, 华人占58%; 在加州, 华人占25%。东西方的文化的冲撞使排外主义思潮再度在华人问题上狂泛。特别是1880年以后, 百万计东南欧移民涌入美国, 掀起了美国移民史上的第二次移民浪潮。新移民在人种、经济、技能、语言、宗教、教育等方面都与1880年前来自西欧、北欧的老移民截然不同, 使新老移民在就业、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冲突和积怨日增。新老移民间的种种冲突随着更多的移民入美扩展到新移民和老移民之间、先来者和后来者之间, 最终演化为一场移民大辩论。第三次移民辩论以1882年《排华法案》为始端, 主要环绕新移民展开。起初辩论局限在经济领域,但随着美国工业文明的进步、一战的结束、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建立、威尔逊 “国际新秩序”理想的破灭、国内传统价值观的巨变, 使美国上下笼罩在“异邦恐惧”和“红色恐惧”的阴影下。反移民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将国内种种矛盾归结为“异邦人的渗入”, 把种族歧视从单纯的对黑人歧视转向对所有新移民的歧视, 拉开了对移民文化、种族大辩论的序幕, 把移民辩论从表面的“经济辩论”转向更深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辩论。辩论导致了《1921年外籍人移民美国限制法》和《1924年移民法》的出笼。这两项移民法对民族来源的限额, 特别是对东南欧和亚洲移民的数目限制, 制止了贫困国家的移民潮, 最终关上了自由移民的大门。虽然美国在二战后期出于反法西斯的需要, 在冷战期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 于1943年废除了1882年排华法案, 1952年颁布了移民归化法, 但均未引起全国范围内的移民问题大讨论。甚至当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促使美国政府对移民政策重新审视和修改, 将民族来源限额制转向全球限额制, 颁布了《1965年移民法》后, 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也仅局限在国会辩论范围内。其缘由是: 第一, 从1924年至1980年美国尚未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潮; 第二, 美国经济在二战后呈“腾飞”势头, 因而引起移民辩论的最主要的“经济”因素不存在; 第三, 经济的繁荣。经过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洗礼”, 美国社会开始对移民持欢迎和宽容态度。美国社会的宽松环境加速了已进入美国的移民对美国价值观认同的上升,“移民”已融入美国社会。为此, 第三次移民大辩论的上限应为1880年, 下限应以1924年为准。 (四)20世纪80年代, 数百万计的东南亚难民和拉美国家的移民、难民和非法移民涌进美国, 这是美国移民史上第一次接受来自第三世界的合法和非法移民及其难民。这一现象是美国移民政策制定者所未曾料及的。仅在1980年一年中, 就有12万古巴人涌进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KeyWest)。与此同时, 越南船民和海地难民也纷至沓来, 特别是墨西哥非法移民借助天然的地理优势, 源源不断地穿越墨美边境。由于他们特殊的移民身份, 便利的地域条件, 对母国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 因而对美国的主流文化持观望态度。移民的文化孤立态势和移民数目集中、人种庞杂、个人素质参差不齐, 引起美国公众舆论的关注, 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再度在美国掀起。这次大辩论的最大特征之一是, 反移民情绪来自非盎格鲁- 撒格逊族裔集团, 特别是1880年以后移入美国的各族裔集团。甚至那些稍早一点到达美国的美籍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对第三世界移民潮的反应也是:“来美国的移民真是太多了。”
其次是民意测验结果的一致性, 即反对移民的无控性。1992年全国性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 69%美国公民赞成取消1990年移民法, 55%的人赞成在新移民法出台前冻结移民。1993年《新闻周刊》民意测验发现, 60%的美国人认为移民对美国是一件坏事, 62%的美国人认为移民夺走了美国人的饭碗。1994年加州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 几乎一半以上的加州人赞同对宪法中“凡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人即为美国公民”的条款进行修改, 以取消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的美国公民资格。辩论除导致《1986年难民法》、《1990年移民法》、《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及移民责任法》的颁布外, 还导致了美国公众舆论的转向, 即从20世纪80年代对第三世界非法移民及难民的 “人道同情”转向90年代对他们的一致性排斥。在第四次大辩论中,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非法移民和难民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 特别是对美国主流文化造成了文化冲击波。鉴于文化影响的潜在性、无序性、长久性, 有关移民的第四次辩论并没有终结, 它将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兴衰、文化冲突的增减而由高降低或由低升高。二在美国四次移民大辩论中,辩论主题始终环绕五个方面展开, 即人口、经济、文化、政策和伦理。人口辩论主要环绕: 多数人与少数人的人口结构; 人口与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 人口与种族。从美国移民史上看, 在1880年至1924年和1980年至今的两次移民大潮中, 由于移民的人数太多, 人种与老移民截然不同, 因而关于人口的辩论主要集中于这二次大辩论。20世纪初,盎格鲁脉系者担心美国社会的多数人的地位(指盎格鲁种族)将被新移民取代。而现今大多数的美国人则担心亚裔移民的高生育率趋势将使白人变为美国的少数人。这种“移民人口威胁论”实质上是种族主义者排斥外来移民的一种手段。本世纪初劳联主席塞缪尔·冈伯斯就抛出了“美国白种人与亚洲人的种族差异永远不会消除, 优等白人必须通过法律排斥低等亚洲人,如果必要,可以诉诸武力”的观点。同时期的评论家乔治·威廉·柯提斯则把素质低的移民称作“在美国民族的血液里注水”。
反对“移民人口威胁论”者认为, 美国的种族来源限制法控制了移民人数, 移民法中的优先权条款使大批优秀移民进入美国, 帮助了美国建设, 移民的同化和对美国认同率的上升使移民已融入美国主流文化, 因此“人口威胁”不存在。在第三次移民大辩论中, 著名评论家珀西·S.格兰特在1912年4月的《北美评论》上著文, 抨击美国负责苏联事务的执行秘书普雷斯科特·F. 霍尔的“血统论”。他在文中大量引用当代自然科学权威人士的科学成果, 以具体事例证明 “融合是进步的法则”,“环境影响比遗传更重要”。
除种族主义者外, 环境主义者大都对移民人口问题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移民人口增长使自然资源殆尽速度加快, 环境污染严重。这种将移民人口的增长与环境破坏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美国移民大辩论中的新观点。但拥护移民者认为, 正是移民的大量涌入才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问题引起美国人的重视并已得到改善。知识界对大辩论的参与是该时期辩论的一大特色。1906年波士顿知识界发动了一场“优生学”运动, 把优生基因作为科学依据, 声称移民限制是保护美国种族纯洁的方法。著名小说家杰克·伦敦在其小说中将种族之战描述为美国日尔曼人种在混血的东南欧移民中沦陷。经济专家威廉·Z. 里普利在其《欧洲人种》一书中将欧洲人种分为北部的条顿民族、中部的阿尔卑斯人种和南部的地中海人种。1908年, 他依据基因理论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人种异化的危险。”1916年, 纽约作家麦迪逊·格兰特在《一个伟大民族的衰亡》一书中从优生学、遗传学的角度呼吁“种族纯洁”, 排斥阿尔卑斯、地中海、犹太人种, 以保卫日尔曼民族的纯洁性。与此相反, 1907年犹太裔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其创作的《熔炉》剧本中将美国喻为上帝的熔炉, 所有的民族在这熔炉里融合成一个新的人种。1915年犹太裔哲学家霍勒斯·卡伦在《民族》周刊发表“民主诉熔炉”论文, 第一次提出文化多元的观点。知识界对辩论的参与使移民问题从单一的社会性论题转向学术性论题, 为当代移民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史料。
经济辩论贯穿每一阶段的移民大辩论。辩论双方主要围绕“移民劳力的质量”、“移民的进取精神”、“移民需求与劳力饥荒”、“移民与美国收入标准和生活标准”、“移民与贫富不均”、“移民与就业”、“移民与福利”、“移民与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等方面展开。在辩论中, 本土主义者认为,“美国是美国人的”, 移民廉价劳动力把原属于美国人的工作夺走, 移民是美国经济的负担。工联主义者认为, 无技术移民降低了劳动质量和工资标准, 最终导致美国人生活标准下降, 贫富鸿沟加深。更有部分经济学者认为, 移民积累资金的回流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相反, 大多数扩张主义者对移民持肯定态度, 他们认为美国西部开发、铁路建设、工厂和工矿的繁荣是与移民的参与分不开的。移民的才干和随身携带的大量资金, 促进了美国的发展。另有经济学家认为移民高强度劳动使劳动产品时间缩短, 成本降低, 消费增长, 服务行业壮大, 就业机会增多。一些社会学家认为, 移民承担蓝领工作使许多蓝领阶层的美国人进入白领阶层, 中产阶级队伍壮大, 美国本土贫富差距缩小, 美国民主得以保证。有些社会学家认为, 移民助长了美国本土人的懒惰恶习, 致使社会闲职人员增加, 国家福利负担加重。鉴于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 有关移民经济辩论的话题最多、参预的人最广、辩论的时期也最长。语言的同化功能在学术界仍是一个争议纷纷的话题。早在1839年, 宾夕法尼亚就通过一项法令, 允许公立学校在拥有30%的家长的请求下可用德语授课。1890年威士康星州颁布了“贝尔特法”, 规定公立学校一年间至少要用英语授课16周, 开创了语言同化的先河。1917年, 为控制东南欧和亚洲移民, 美国国会通过文化测试法以阻止低质、文盲移民入美。在双语教育问题上, 赞同把语言同化作为促使移民对移往国认同的美国人担心, 如果移民保留他们的语言, 他们就不愿意或无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同时,移民的母国语言的保留将削弱美国文化的同质性, 因而不利于移民的同化和保证美国同质性文化的完整。美国著名作家布克·T. 华盛顿在结束其对欧洲考察后写道:“我非常害怕这些人将大批地涌入我国的郊区。在那里他们较少有受教育的机会, 能保持他们母国的习俗和语言, 因而我们将遇到比黑人种族还要困难, 还要危险的种族问题。”社会学家丽拉·米歇尔斯·阿奇森认为,“双语教学”将鼓励移民不忠于美国, 因此她提倡“单语教育”。同时她还告诫国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永远强大, 除非他们将其民族的伟大理想同化为一种水晶般的民族文化。”但挪威移民、《挪威语报》编辑沃德马·阿格则认为:“没有任何站住脚的证据表明一个人因为仅会说英语便可证明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他认为外语报刊有助于英语差的移民加快美国化进程, 因为这些报纸将有关美国社会的信息传给了这些移民, 因此双语教育有利于新移民的同化。但20世纪90年代末, 美国双语教育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1998年由硅谷巨富罗恩·斯昂提出的《教孩子学英语》的提案成为加里福尼亚1998年竞选话题。提案的目的是要彻底取消加州的双语教育。提案要求公立学校的所有学生均接受以英语为主的教育, 除非他们的父母有其他特殊请求。不通晓英语的学生将被安排进“英语强化班”, 培训时间通常不超过一门。该提案受到自称代表移民利益的社会活动家的反对, 但却意外地获得拉美裔选民和其他移民的强劲支持。
《洛杉矶时报》新近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 84%的拉美裔移民声称他们将支持该提案, 其比例甚至高于白人选民(80%)。移民选民对双语教育的否定使双语教育似乎走到尽头。在移民政策辩论中, 第三次移民大辩论是移民政策大出台时期。自1882年“排华法案”开创了移民的排斥时代后, 一系列移民限制法、排斥法相继出笼。1891年国会禁止弱智、残疾、乞丐、传染病患者、罪犯、重婚者进入美国, 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1903年国会颁布“排斥无政府主义者”法案, 第一次建立对移民政治观点进行考察的制度,以防止“麦金莱事件”的再度发生。1907年的《流放法》、1908年的日美《君子协定》、1917年的《文化测试法》、1921年的《移民限制法》、1924年的《民族来源限制法》, 均展示了美国本土人对新移民的强烈的种族歧视和病态的“恐外”心理。移民伦理辩论穿插于移民政策辩论之中, 但有别于政治辩论。它所涉及的辩论主题是非法移民的权力、人道主义移民政策与国家利益。这一辩论主题在第四次移民大辩论中尤为突出,特别是关于非法移民的权利辩论。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非法移民无权呆在美国, 他们理所当然地无权享受合法移民和美国公民所享受的一切权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生而平等”, 既然他们是人, 他们就有权享受美国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权力。人权主义者呼吁移民政策应体现“人道和人权”, 但现实主义者则不以为然。他们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一切有损国家利益的人道主义”是“非人道主义”, 因它置美国人的利益而不顾。移民辩论的五个主题相互穿插、互为依存、互为影响, 在一定前提下互为转换。因此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不应陷于一种单向的、直线的研究模式之中, 它应是一种多层面的研究, 同时也是一种跨历史、跨学科的研究。
1034 P.O. Box
Hollywood,CA 9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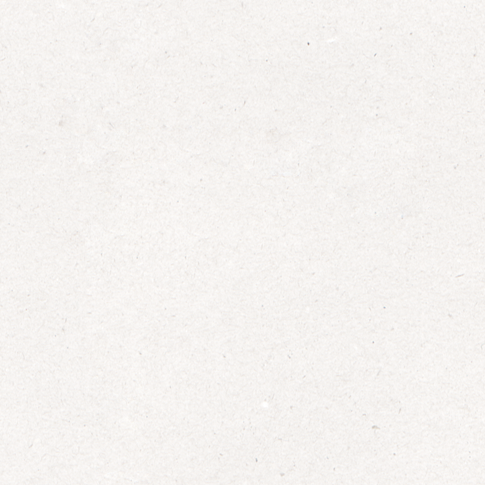
Tel: 323-208-9788
Fax: 323-208-9788
info@yiminlawyers.com
请将微信号或电话号码发邮箱,美国执业移民律师将直接联系您!




Copyright © meiyi. All Rights Reserved.